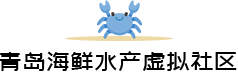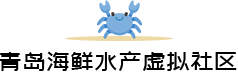台州俚语中的海腥味
作者:王寒
外地人初到台州,闻到空气中咸湿的鱼腥海味,有点不习惯。但在台州人的嗅觉里,那不是海腥味,而是鲜味。台州人热爱家乡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台州的海鲜实在太丰富太美味了。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台州人的口福真是没得说,漫长的海岸线保证了台州人一年到头海鲜不断。到台州的酒楼吃饭,一楼“点菜房”的玻璃柜里、桌板上、地上,到处都是生猛海鲜,任君挑选,活杀现烧。吃完海鲜,喝完啤酒,把嘴一抹,打个响亮而自豪的饱嗝,做人那叫一个痛快!
海鲜吃多了,说话也难免沾点腥气,台州人比别地方的人更喜欢拿海鲜说事,到温岭、玉环、椒江等地走走,冷不防就会听到一连串带海腥味的俚语俗话。
台州人说人嘴小,不说樱桃小嘴,而是说“鲳鱼嘴”。某台州人在电话里向姐姐介绍新任女友的长相,说她长得比前一个漂亮多了,“鲳鱼嘴,沙蜂腰。”外地同事听后几乎厥倒。台州人观察力不可谓不强,可不,鲳鱼身材扁平,嘴巴十分小巧,不像胖头鱼之大头肥唇。不过从美感角度而言,鲳鱼嘴毕竟不及樱桃小嘴之红润,鲳鱼嘴再小,看上去白惨惨的,像贫血病人,让人产生不了一亲芳泽之欲望。把女友的樱桃小嘴,说成“鲳鱼嘴”,大概也只有台州人了。除了“鲳鱼嘴”外,还有“虾皮眼”,言人眼小,也颇为传神。
某人性格绵软,或者精神委顿,有气无力,台州方言形容为“软潺”。潺指的是水潺,水潺是一种软体鱼类,体狭长而前宽后细,色灰白光滑,半透明,含水份多,肉质细嫩,全身无刺,仅一根软骨,又称龙头鱼、豆腐鱼。别看水潺不起眼,红烧水潺、咸菜水潺的味道极佳,汪曾祺曾著文夸过它的美味。台州人把软弱无能者,一律称为“软潺”,颇有轻视之意,亦十分形象。水潺从外形上看,的确柔若无骨,实际上,它锋利的牙齿吞得下数倍于它的海鱼,剖水潺时,经常能从它的肚子里挖出小鱼。可见,水潺外形上的软,很具有蒙蔽性,实际上,它的凶残并不亚于其他的海洋生物。
海边人说,“正月雪里梅,二月桃花鲻,三月鲳鱼熬蒜心,四月鳓鱼勿刨鳞”。的确,台州南边县市的人谁不知“三鲳四鳓”,农历三月鲳鱼的味道最鲜美,而到了四月,该尝尝鲜嫩肥美、口味鲜香的鳓鱼了。鳓鱼双眼炯炯、向外凸起,而且眼睛是血血红的,像得了红眼病。台州人喜欢吃鳓鱼,却把那些嫉妒人钱财的人称鳓鱼眼,或者索性就叫“红眼鳓鱼”。而与红眼鳓鱼相对应的,则是“白眼泥螺”——泥螺离开滩涂久了,会泛白。
“公”一般用来尊称,老公是私的,却以“公”称之。钱是个好东西,所以财神称为赵公元帅。而台州人用“虾公”泛指驼背,委实形象不过。我小时候,听到爱开玩笑的邻居,把驼背的看门人称为“虾公”,以为此人姓夏,跟着叫夏公公。稍大些,才知台州人是以虾公泛指驼背。
女友带我到温岭钓浜的海滩玩,小资的她在沙滩上晒起日光浴,当地朋友打趣她为“晒鲞”。台州人把仰卧或太阳底下曝晒称为“晒鲞”。其实,正宗的晒鲞是腌制干货的一道程序,石塘、松门等海边渔镇的男男女女,一到丰收季节,就忙着晒鲞,台州的画家和剪纸艺术家也把晒鲞当成渔家特有的风情来表现。
台州出产鲞,品种颇多,有黄鱼鲞、墨鱼鲞、乌狼鲞(乌狼者,河豚也)、鳗鲞,光是大黄鱼鲞就可分瓜鲞、老鲞、潮鲞、无头鲞、老虎鲞等。台州的鲞,名声在外,是谓台鲞,尤以温岭松门出产的为最,闻名全国。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上提到台鲞时,流着口水赞叹道:“台鲞好丑不一。出台州松门者为佳,肉软而鲜肥。生时拆之,便可当作小菜,不必煮食也。用鲜肉同煨,须肉烂时放鲞,否则鲞消化不见矣。”台鲞最妙之处在“杀饭”,夏天天气炎热,胃口不开,吃什么都味同嚼蜡,一碗黄鱼鲞端上来时,又咸又鲜,让人食指大动,一碗饭下肚了,还想再吃一碗。这鲞的诱惑力着实大着呢,鲞头交给人看管,都有偷吃的嫌疑,何况交给猫看管。所以台州俚语中的“鲞头交拨猫望”,指用人不当。
除了黄鱼鲞、带鱼鲞、鳗鱼鲞外,海边还有各种各样的咸鱼,海边人喜食咸货,咸带鱼、龙头烤都是经过曝腌的,极咸。咸鱼既腌渍,自然复活无望,所以“买咸鱼放生”之举,用来形容徒劳无益。
在海鲜中,还有一种最不起眼的东西叫虾虮,虾虮是海洋浮游生物,虾籽般大小,旧时贫苦人家以虾虮下饭。台州话里的“烂虾虮”,指不值铜钿的货物。虾虮虽然不起眼,不过亦有人爱极,以为美味无双。虾虮经盐糟渍而虾酱,味鲜香浓,被喻为调味之冠。虾虮如此微不足道,自然无法兴风作浪,所以台州话里“虾虮作勿起大浪”,指不可改变的事,“虾虮作大浪”,指的是不自量力。
台州北边的山里人常分不清墨鱼、鱿鱼、章鱼、望潮、鲑蛄的区别,他们一律称为乌贼。海边的人绝不会搞混这几者的关系,我认为这些海鲜中,以望潮最为美味。望潮是章鱼的婴儿期,出生没多久的章鱼叫望潮,两个月大的时候,称为鲑蛄,这似乎是台州特有的叫法。我爱极望潮的鲜美,视清汤望潮为人间至味。烹饪望潮极简单,把水烧滚,放上姜、盐,只须把望潮往烫水里滚上一滚,盛上来用醋一蘸,鲜得让人不知今夕何夕。台州话里“墨鱼笑鲑蛄”,指的是五十步笑百步的事,与这句俚语相类似的是“老鸦笑猪乌,勿晓得自己满身乌”。
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有一处点睛之笔:“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两个女子,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得不到的东西总是最好的,得不到的爱最值得人怀想,当然,这不仅仅局限于感情。对此,台州人也有一句带海腥味的俚语——“逃去的鱼大”。
台州人喜欢吃蟹,尤其喜欢拿蟹说事,台州人管不死不活、名头响、却没花头的人叫“死白蟹”,俚语就有“台州府人死白蟹”一说,临海旧时是千年台州府,此俚语是说生活在千年台州府的人,虽然名头响当当,其实没冲劲,没活力,没大花头。一个人做事随便,无主见,就称他是“大水蟹”,大水蟹是随水漂流之蟹。劫夺别人夺取而来的财物则是“倒壳蟹”。台州人以“空壳蟹”喻外强中干的人,以“软壳蟹”喻胆小怕死的人,其实,软壳蟹不好听,但软壳蟹的肉极其细嫩。台州人喜欢拿“蟹血”、“蟹子”当口头禅,言其子虚乌有,因为蟹无血也无子。醉汉或怒汉的红脸,谓之“落镬的红蟹”。“跛足蝤蠓现成洞”,有傻人傻福的味道。“沙蟹爬进盐缸里”,意谓自寻死路。除了这些,还有“讨饭人撮死蟹——只只好”,“一只手柯勿牢两只蟹”,意谓做人不要太贪心。
台州人对海鲜太熟悉了,他们喜欢借海鲜说事,有关海鲜的俚语张嘴便来,这些俚语既入木三分,又接地气,委实形象生动,谁说台州人只有赚钱细胞没有文学细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