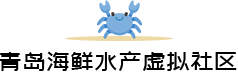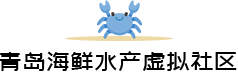从我家搭地铁去杭州东站,跟着坐上高铁至上海虹桥,换上海10号线,然后从“陕西南路”站出来抬头看见上海的天日,大概需要两个小时。
上海不少偏远郊区的人去同样的地方,绝对要比我花更长的时间,转换更多的交通工具。
总之,我常常挑选从“陕西南”站出来,像一只小小的鼹鼠,站在阳光或微雨之下,与上海觌面相见。
和地铁相连的那个建筑现在叫“环贸”,之前是襄阳路小商品市场,再之前,民国时候,叫陈伟达饭店,一家老外开的高级酒店公寓。
七七事变前一年,因为打战,很多人涌进上海租界躲避,其中就有张爱玲的舅舅,带着一家老小,在陈伟达饭店开了一个房间“避难”。张爱玲也在此住了俩星期,等到她回家时,继母因她在外面住没有和自己打招呼,“你眼里哪儿还有我呢”,在张爱玲的叙述里,继母不知道是不是积愤泄洪,和她吵了几句后,竟然打了她一个耳光。随之而来,张爱玲的父亲也赶来打了她一记耳光,并将她幽禁起来。这一场折辱,打得少年张爱玲的“恋父情结”碎了一地,待要重新拼接粘贴起,得等到她的暮年,在四季如春的洛杉矶了。
关于洛杉矶,不知道为什么,我首先想到的竟是陈冠希说过的一句话“我的根在洛杉矶”,因为洛杉矶在他最失意时收留了他。
其实张爱玲亦是如此。但是张爱玲从来不会这么煽情——抑或,叫“深情”?
她身上有一种决绝的冷,像冰块上的那朵白雾。
《私语》,《小团圆》里都写过上面那段故事。可以说,因为在这饭店住的两星期,张爱玲的命运由此改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也由此改变。
但是,当我地铁,高铁,再换乘另一个城市的地铁到达时,这家饭店早已了无踪迹,连曾经闹猛的襄阳路小商品市场都早已了无踪迹了,一切,就像它们从来都不曾存在过一样。时间真的是一块抹布,把一切重要的,不重要的东西,都抹的干干净净——世法平等干净之余,印证了一句箴言“凡所有相皆虚妄,皆为颠倒梦想”。
现在有的是什么呢,是“环贸”,卖一些潮牌,从环贸的某些专柜穿过,年轻的服务员小妹,小哥们,有些还会微笑着上来兜搭:“阿姐,你穿的挺潮的唻”……
有一种淡淡的怅惘与恍惚油然而生,那是“抹布”永远都抹不去的。
我常常觉得杭州与上海的链接,是一直处于在一种地下状态的,从我搭上杭州的地铁开始,我就有两个小时没有接触到户外,没有接触到户外真实可感的阳光与微风了,一旦出来,必须(当然也是我自己选择的地铁出口)穿过环贸,穿过这家与张爱玲有关的建筑物,然后,将自己置身于淮海路陕西南路上。
陕西南路,原来叫亚尔培路,这名字绝对比前者好听。
走到这里了,我这是要去哪呢,我,准备去红房子吃西餐。
陈丹燕《慢船去中国》的开头这么写道:
“陕西路交界的街角,红房子西餐馆的门前,尽是在路灯下匆匆往家赶的人和车……陕西路上的人行道也很窄,除了法国梧桐占了的位置,只有两三个人可以擦肩而过……所以,当这家人停在红房子西餐馆门口的时候,人行道被他们挡住,于是,不停的有人粗鲁地撞着他们,或者擦着他们的身体穿过去,冲乱他们的队伍,有人嘴里不耐烦地埋怨他们挡住了路。而他们沉默着,既不生气,也不着急和退让,还是按照自己原来的速度,各自鱼贯而入。
因为知道红房子西餐馆的门廊小,所以先进去的人就往底楼的店堂里让。但是,他们并不象当时没有规矩的客人那样,自己在店堂里乱撞,而是等着跑堂的上来招呼。他们也不象有的集合好一起来吃馆子的人,彼此大声招呼,发出兴奋的声音。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进门的时候,还是象生客人那样踉跄了一下。这红房子西餐馆,是从太平洋战争以前的汽车间改造过来的,不是正规的房子,所以,一进门就有两级往下走的台阶,只有常来这里的熟客人才知道一进门就得下楼梯,才不至于跌跌撞撞。
红房子西餐馆的门,虽然是那种欧洲小餐馆式的镶玻璃门,但还算厚实,一旦关上,站满了人的门廊里突然一静。一股咖啡,番茄沙司,融化的奶酪和新鲜油炸食物的西餐馆气味便扑面而来。”
陈丹燕小说中写的去红房子西餐馆吃饭,是1989年,那时候,上海人去红房子吃一顿大菜,还是一件极其隆重的大事,而现在是2018年,红房子早不在“汽车间”了,它的一楼狭窄如电梯间,吃饭得上二楼,也有三楼,电梯按钮三楼上写着“红玫瑰,紫罗兰”,我先还真猜不出那是什么,后来一想,难道是大名鼎鼎的红玫瑰,紫罗兰美发厅?现在国营理发厅式微之后,都搬到这里来了?
唐颖有一部小说叫“红颜”,有一年拍成了电影,由霍建华和关之琳主演,片名为“做头”,俩人做头做到做爱的那家店,原型是红玫瑰还是紫罗兰?
记得“红颜”开篇第一句,“爱妮坐在亚尔培美发厅里”,可不就是这儿附近嘛。
和我一起上电梯的还有一个上海男人,见我按2楼,就提醒说,红房子要5点才营业,现在还早,你先去逛一下街吧。他按的是3楼。
后来我寻思,他是楼上的理发师?但我常见的理发师,大都打耳钉,有纹身,发型奇特或夸张,而他一如普通的上海男人,公司小职员之类。不过他的态度温和友善,有一种江南老派男人特有的斯文和殷勤,似是来自老上海滩遗韵。
一开始,我以为现在应该没什么人会来红房子吃饭了,又不是什么节假日,外加上海那么多加西餐厅,创意餐厅,还会有什么人和我一样,来红房子吃“大菜”呢。
后来发现我错了。5点不到,就有不少人在等位,看起来大都是本地人,有两对是老年夫妇。其中一对比较打眼,伉俪俩明显都是仔细收拾过的,丈夫穿着西装,妻子更是描眉画眼,有一种隆重出席的意味。
那个女客还烫着一头,大约就叫作老式“大波浪”的头发,因为刻意去店里吹过,做过发型,一丝不苟,一看就知道是理发师的作品,自己买个卷发棒,或者由家里的美发票友来做,那是根本出不来的。
以我的审美看过去,这发型有点怪。怪在什么地方呢,怪在一丝不苟,每根头发,每个卷,都像在告诉大家:我可是精心做出来的。
太过雕琢,未免死板。据说八十年代很流行这种款式,和现在的随意风完全不同。
我的理发师有一次和我说,其实我的发型也可以叫大波浪,当然我只烫了一半,头发的另一半,上半部分,还是直发,他说给我吹头发,专业叫“手吹大波”,必须手工吹出随意感,空气感来,想要借助美发工具速成都是不可能的。
但,像这位女客可能根本看不上我的“大卷”,因为不够卷,而她的每一个小卷都很挺刮,都很卷曲,每一只都彼此相象,发量均匀,代表了另一个时代的审美,我现在在杭州几乎没有见过有类似的阿姨们顶着这么一脑袋精雕细琢的小卷卷,卷的那么矜持而僵硬。
杭州和她同龄的女性一般要么在跳广场舞,在广场上蠕动着肥硕的身段,胸前,小腹垒起如小山:要么——我还真很少接触她的同龄女性,倒是常常看到她们在校门口接送孙女外孙子之类。
但她还和丈夫一起出来吃西餐,而且还是红房子。尽管红房子的装修花哨而廉价,服务员全是本地老阿姨,全讲一口上海话——她们大约对着奥巴马川普也要讲上海话的,掺杂是一种土著的骄傲与自豪:侬吃点啥物事啦,总统先生?
她身上一件簇新的红色外套,很正式的那种,脸上也极其认真地施以脂粉,唇膏是正红色的,属于上个世界的彩妆流行色。客观地说,杭州的阿姨们,却明显要比她落后。
同龄的杭州老阿姨们,除非家境优越本身又受过教育的,在或文艺或雅静的环境里一直生活的人,否则,再有钱的都看起来比较粗鄙与市井。
杭州的“她们”也常常出去就餐,下馆子,而且机会肯定比别的城市的女人多。因为杭州游宴之风盛行,家家都喜欢出去吃饭。但她们肯定不去吃西餐,最受她们欢迎的店是外婆家,新白鹿,绿茶……又便宜又“好吃”(实在是见仁见智),又有归属感。
红房子之类,那叫啥嘛,有啥吃头。另外“她们”都喜欢热闹,老两口一起吃饭没意思,哪儿比得上呼朋唤友,呼姐唤妹,或者拖着一家老少吆五喝六地一起吃饭有劲呢——以上开出单子的那几家饭店,请大家尽量避免去就餐,如若很不幸和这些阿姨以及他们的家人“同框”,我也总要求换个位置,哪怕独自坐在厨房门口。
瞥见那个红衣大波浪阿姨极认真地看菜单——我想象不出她有什么可看的,她肯定不是第一次来,餐单又不是小说更新,每次都得重新看一遍。
我以前吃过两次,稍微浏览了一下,点了“洋葱汤。罗宋汤。虾仁杯。炸猪排。烙蛤蜊。烙蟹斗。”
不久那大波浪阿姨也点完,认认真真地把餐巾平铺在腿间。我突然童心大发,向朋友表演把餐巾塞进衣领,类似小宝宝围嘴的铺法——别以为这是失仪,很多罗宋人(俄罗斯人)吃大餐都是这样的,这亦算是规矩之一吧。
很快我感觉到自己的轻佻,毕竟这是法式餐厅,我这么“恶搞”,是对大波浪阿姨以及红房子的不尊重,于是,我也“吾从众”,把餐巾规规矩矩地铺好。
菜上来了,大波浪阿姨和她的丈夫吃的非常认真。我和同行的朋友一起感叹,炸猪排不如街上烤串店的,蛤蜊没入味,,最后用军用飞机运回北京的虾仁杯,差强人意;
法国菜是比较腻的。听说法南的乡下菜,比如普罗旺斯啥的,更是腻的死人。我只好这么安慰自己。
“我们来这儿吃,是因为我们是游客,想不通他们本地人还这么郑重其事地来这里吃,为什么?真的不好吃呢。”朋友问我。
我说,可能对于上海人来说,从50年代开始,普通人家,中等人家,乃至于明星名流,都以在红房子吃大餐为正宗,为体面,像大波浪阿姨他们,年轻时也许消费不起,等到老了,为一偿心愿,穿上参加婚宴的行头来这里就餐,或许就是为了圆梦。
他们在心里说不定也耻笑我们呢,耻笑我们穿着破洞卫衣,乞丐风牛仔裤,镂空靴子,素颜无妆,把这儿当麦当劳了吧,搁从前,那是连大门都不会让你进的。
而我,为什么要去红房子吃西餐呢?
年少时,江南潮湿多雨的季节里,我每天一页一页地读着闲书,发黄的书页咔咔作响,读的大都是海派作家,我从小喜欢看关于上海的文字,从海上花列传,歇浦潮,海上繁花梦,人间地狱,歌场冶史……从海派作家韩子云,海上漱石生,毕倚虹,,汪仲贤……到后来大名鼎鼎的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陈村,程乃珊,唐颖……无论好坏良莠,我大都找来看过。
或许,那也不叫看,叫“蚕食”。
那个时候,某家中学附近的市民读书馆里,总有一个背着书包的少年,像只蚕一样,每天还两本书,借两本书。
她手里的书,大都是关于“上海”的。
上海是个海。这个海,是由书籍,由想象,由各种时空里不同人的叙述,精卫填海而成。
因此,对于我来说,上海,那是“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是一种最缥缈,也是一种最熟悉;是一种最艺术,也是一种最现实。
在我还不没有踏进亚尔培路之前,我就知道这条路上的红房子多有名,而对过是国泰电影院,张爱玲在这里看过电影,看完电影去对面老大昌吃咖啡和蛋糕,再多走几步路是花园饭店,老毛来上海就住这儿,《繁花》中的某一个上海女人,在此邂逅一个寂寞的日本老男人……
那条长路的每一条分支,每一个路口,每一幢房子,都有故事,都有风月。
上海,从小就是我仰望的情人,但我的情人是藉由文学塑造出来的,所以活色生香。真实的色相当然要差一层,平凡一层,暗淡一层,但,我根本不在乎。
时过境迁,我的同乡们很喜欢以“上海才是杭州的后花园”,“我们杭州”现在就是比上海干净,新,发达,某些设施领先自诩,而上海,确实如一位熟年美人,渐渐褪去曾经那不可一世的风华。
但,地理上的上海如是,而文学上的上海却永远不会如此。
这就好比,真正的红房子西餐水准一般,但小说里,各种回忆文章中,传说中的红房子西餐,却永远类似于一场盛宴,堪比韩熙载夜宴图,声色浓丽不可再得。
我想,真正的盛宴大抵,或者说只能是产生自意想与文学艺术之中的。生理上的美味感很难获得(人总是好吃的吃的越多,越感觉没什么东西好吃),意想中的美味却会一直牵引着我们在迢迢时空里寻觅与跋涉。
作者:罗衣一时聚散 金学红学研究者 言情小说作者 专栏作者 独立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