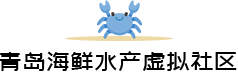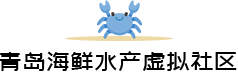关荣魁行二,他又姓关,后台演员戏称他为关二爷,或二爷。他在科班学的是花脸,按说是铜锤、架子两门抱。他会的戏不少,但都不“咬人”。演员队长叶德麟派戏时,最多给他派一个“八大拿”里的大大个儿、二大个儿、何路通、金大力、关泰。他觉得这真是屈才!他自己觉得“好不了角儿”,都是由于叶德麟不捧他。剧团要排“革命现代戏”《杜鹃山》,他向叶德麟请战、他要演雷刚。
叶德麟白了他一眼:“你?”
——“咱们有嗓子呀!”
——“去去去,一边儿凉快去!”
关二爷出得门来,打了一个哇呀:“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茶壶当夜壶,哇呀……”
关二爷在外面,在剧团里虽然没多少人捧他,在家里可是绝对权威,一切由他说了算。据他说,想吃什么,上班临走给媳妇嘱咐一声:
“是米饭、炒菜,是包饺子—韭菜的还是茵香的,是煎锅贴儿、瓤榻子,—熬点小米粥或者棒茬儿粥、小酱萝卜,还是臭豆腐“他要是不给做呢?”“那就给什么吃什么叹!”关二爷回答得很麻利。“哦,力巴摔跤!”(北京的歇后语,“力巴摔跤,给嘛吃嘛”。)
申元镇会的戏很多,文武崑乱不挡,但台上只能来一个中军、家院,他没有嗓子。他要算一个戏曲鉴赏家,甭管是老生戏、花脸戏,什么叫马派、谭派,哪叫裘派,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小声示范,韵味十足。只是大声一唱,什么也没有!青年演员、中年演员,很爱听他谈戏。
关二爷对他尤其佩服得五体投地,老是纠缠他,让他说裘派戏,整出整出地说,一说两个小时。说完了“红绣鞋”牌子,他站起要走,关二爷拽着他:“师哥,别走!师哥师哥,再给说说!师哥师哥!……”——“不行,我得回家吃饭!”别人劝关二爷,“荣魁,你别老是死乞白咧,元镇有他的难处!”大家交了交眼神,心照不宣。
申元镇回家,媳妇拉长着脸:
“饭在锅里,自己盛!”
为什么媳妇对他没好脸子?因为他阳疾。女人曾经当着人大声地喊叫:“我算倒了血霉,嫁了这么个东西,害得我守一辈子活寡!”
但是他们也一直没有离婚。
叶德麟是唱丑的,“玩艺儿”平常。嗓子不响堂,逢高不起,嘴皮子不脆,在北京他唱不了方巾丑、袍带丑,汤勤、蒋干,都轮不到他唱;贾桂读状,不能读得炒蹦豆似的;婆子戏也不见精采;来个《卖马》的王老好、《空城计》的老军还对付。老是老军、王老好,吃不了蹦虾仁。
树挪死,人挪活,他和几个拜把子弟兄一合计:到南方去闯闯!就凭“京角”这块金字招牌,虽不能大红大紫,怎么着也卖不了胰子(北京的军乐队混不下去,解散了.落魄奏乐手只能拿一支小号在胡同口吹奏,卖肥皂,戏班里称他们“卖了胰子")。
到杭嘉湖、里下河一带去转转,捎带着看看风景,尝尝南边的吃食。商定了路线,先到济南、青岛,沿运河到里下河,然后到杭嘉湖。说走就走!回家跟媳妇说一声,就到前门车站买票。
南方山明水秀,吃食各有风味。镇江的膏肉、扬州富春的三丁包子、嘉兴的肉粽、宁波的黄鱼誊笃肉、绍兴的梅干菜肉、都蛮“崭”。使叶德麟称道不已的是在高邮吃的喝嗤鱼余汤,味道很鲜,而价钱极其便宜。
南方饭菜好吃,戏可并不好唱。里下河的人不大懂戏,他们爱看《九更天》、《杀子报》这一类剖肚开膛剁脑袋的戏,对“京字京韵”不欣赏。杭嘉湖人看戏要火爆,真刀真枪,不管书文戏理。
包公竟会从三张桌上翻“台漫”下来。观众对从北京来的角儿不满意,认为他们唱戏“弗卖力”。哥几个一商量:回去吧!买了一些土特产,苏州采芝斋的松子糖、陆箕荐的酱肘子、东台的醉泥螺、鞭尖笋、黄鱼鳌、梅干菜,大包小包,瓶瓶罐罐上了火车。刨去路费,所剩无几。
进了门,洗了一把脸,就叫媳妇拿碗出门去买芝麻酱、带两根黄瓜、一块豆腐一瓶二锅头。嚼着黄瓜喝着酒,叶德麟啃然有感:回家了!
“要饱还是家常饭”,叶德麟爱吃面,炸酱面、打卤面、芝麻酱花椒油拌面,全行。他爱吃拌豆腐,就酒。小葱拌豆腐、香椿拌豆腐,什么都没有,一块白豆腐也成,撒点盐、味精,滴几滴香油!
叶德麟这些年走的是“正字”。他参加了国营剧团。他谢绝舞台了,因为他是个汗包,动动就出汗,连来个《野猪林》的解差都是一身汗,连水衣子都湿透了。
他得另外走一条路。他是党员,解放初期就入了党。台上没戏,却很有组织行政才能。几届党委都很信任他。
他担任了演员队队长。演员队长,手里有权。日常排戏、派活,外出巡回演出、“跑小组”,谁去,谁不去,都得由他决定。
,谁不能去,他说了算。到香港演出、到日本演出,更是演员都关心,都想争取的美事,—可以长戏份、吃海鲜、开洋荤、看外国娘们,有谁、没谁,全在队长掂量。
叶队一长的笔记本是演员的生死簿。演员多数想走叶德麟的门子,逢年过节,得提了一包东西登门间候,水果、月饼、酒。叶德麟一推再推,到了还是收下来了。“——下不为例!”——“那是那是!这点东西没花钱,是朋友送我的。”
叶德麟一帆风顺。,原来的党委、团长都头朝下了,,他带来几个“外行”驻进各团监督,有问题随时向他汇报。
但是他还得有个处理日常工作的班底,他不能把原来党委的老班底全部踢开,叶德麟留下来仍旧当演员队的队长。虞部长不时还会叫他去谈话,听意见,备咨询。叶德麟觉得虞部长还是很信任他,心中暗暗得意,觉得他还能顺着这根竿子往上爬几年。
叶德麟也有不顺心的事。
一是儿子老在家里跟他闹。儿子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到处打游击,这儿干两天,那儿干两天。儿子认为他混成这相,全得由他老子负责。他说老子对他的事不使劲,只顾自己保官,不管儿女前途。他变得脾气暴躁,蛮不讲理,一点小事就大喊大叫,说话非常难听。动不动就摔盘子打碗。叶德麟气得浑身发抖,无可奈何。
一件是出国演出没有他。剧团要去澳大利亚演出,叶德麟忙活了好一阵,添置服装、灯光器械、定“人位”,—出国名额要压缩,有些群众演员必须赶两三个角色。他向虞部长汇报了初步设想,虞部长基本同意。
叶德麟满以为要派他去打前站,—过去剧团到香港、日本演出,都是他打前站,不想虞部长派他的秘书宣布去澳名单,却没有叶德麟!这对他的打击可太大了。他差一点当场晕死过去。这不是一次出国的事,他知道虞桧压根儿没把他当作自己的人,完了!他被送进了医院:血压猛增,心绞痛发作。
住了半个月院,出院了。
他有时还到团里来,到医务室量量血压、要点速效救心丸。自我解嘲:血压高了,降压灵加点剂量;心脏不大舒服,多来一瓶“速效救心”!他坐在小会议室里,翻翻报。他也希望有人陪他聊聊,路过的爷们跟他也招呼招呼,只是都是淡淡的,“卖羊头的回家一一不过细盐(言)”。
快过年了。他儿子给他买了两瓶好酒,一瓶“古井贡”,一瓶“五粮液”,他儿子的工作问题解决了,他学会开车,在一个公司当司机,有了稳定的收入。叶德麟拿了这两瓶酒,说:“得咪!”这句话说得很凄凉。这里面有多重意义、无限感慨。一是有这两瓶酒,这个年就可以过得美美的。儿子还是儿子,还有点孝心;二是他使尽一辈子心机,到了有此结局,也就可以了。
叶德麟死了,大面积心肌梗死急性发作。
照例要开个追悼会,但是参加的人稀稀落落,叶德麟人缘不好,大家对他都没有什么感情。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对谁都也没有感情。他是一个无情的人。
靳元戎也是唱丑的,岁数和叶德麟差不多,脾气秉性可很不相同。
靳元戎凡事看得开。,他被精简了下来,下放干校劳动。他没有满腹牢骚,唉声叹气,而是活得有滋有味,自得其乐。干校地里有很多麻雀,他结了一副拦网,逮麻雀,一天可以逮百十只,撕了皮,酱油、料酒、花椒大料腌透,入油酥炸,下酒。干校有很多蚂炸,一会儿可捉一口袋,摘去翅膀,在瓦片上焙干,卷烙饼。
他说话很“葛”。
干校来了个“领导”。他也没有什么名义,不知道为什么当了“领导”。此人姓高,在市委下面的机关转来转去,都是没有名义的“领导”,,这位老兄专会讲“毛选”,说空空洞洞的蠢话,俨然是个马列主义理论家。
,干校都称之为“高政工”。他常常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馒点子。《地道战》里有一句词:“各村都有高招”,于是大家又称之为“高招”。干校本来是让大家来锻炼的,不要求粮量,高招却一再宣传增产。
年初定生产计划,是他一再要求提高指标。指标一提再提,高政工总是说:“低!太低!”靳元戎提出:“我提一个增产措施:咱们把地掏空了,种两层,上面一层,下面一层。”高政工认真听取了靳元荣的建议,还很严肃地说:“这是个办法!是个办法!”
逮逮麻雀,捉蚂炸,跟高政工逗逗,几年一晃也就过去了。
,虞部长,干校解散,各回原单位,靳元戎也回到了剧团。他接替叶德麟,当了演员队队长。
他群众关系不错。他的处世原则只有两条:一,秉公办事;二,平等待人。对谁的称呼都一样:“爷们儿”。
他好吃,也会做。有时做几个菜,约几个人上家里来一顿。他是回民,做的当然都是清真菜:炸卷果、炮糊(炮羊肉炮至微糊)、它似蜜、烧羊腿、羊尾巴油炒麻豆腐。有一次煎了几挡鸡肉馅的锅贴,是从在鸡场当场长的老朋友那儿提回来的大骗鸡,撕净筋皮,用刀背细剁成茸,加葱汁、盐、黄酒,其余什么都不搁,那叫一个绝!
他好喝,四两衡水老白干没有问题。他得过心绞痛,还是照喝不误。有人劝他少喝一点,他说:“没事,我喝足了,就心绞不疼了。”—这是一种奇怪的语法。
他常用这种不通的语言讲话,有个小青年说:“‘心绞不疼’,这叫什么话!”他的似乎不通的语言多着呢!,有一个也是唱丑的狠斗马富禄,他认为太过火,就说:“你就是把马富禄斗死了,你也马富禄不了啊!”什么叫“马富禄不了啊”?真是欠通,欠通至极点!他喝酒有个习惯,先铺好炕,喝完了,把炕桌往边上一踢,伸开腿就进被窝,随即鼾声大作。熟人知道他这个脾气,见他一钻被窝,也就放筷子走人,明儿见!
他现在还活着,但已是满头白发,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