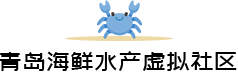扬州炒饭(一)
陈五和赵二都五十来岁,是茶社常客,也是扬州有名的老饕,都有一条好舌头。
赵二是远近出名的馋虫饿鬼。生着个五短身材,八字眼、红鼻头,自带三分醉相,既好吃又好酒。可他的“馋舌”是一绝,专好吃味儿,舌上味觉敏锐,远过常人。一口吃食进了嘴,便有百般滋味儿在味蕾上绽开,同样的一片卷心菜,进了普通人嘴里那就是一片菜,进了他嘴里,就能提格成一桌三头宴。食物咀嚼时,在舌面是什么滋味,在舌边又是什么滋味,他说得极精细。一道菜他只消吃上两口就能把菜里看得见看不见的食材、调料一样不差地都给你说出来,连汤里放了一根笋还是两根笋都瞒不过他。赵二是个苦出身,但天生了这样的异禀,人人都说他嘴上这点福气真个不小。
(磨刀匠)
赵二打小就跟着他爹磨刀,干了一辈子的磨刀匠,近几年才给自个儿退了休。扬州城里这门手艺到现在也还没绝种,小区、村巷里还时不时见有人蹬着三轮儿,吆喝着“磨剪子,镪菜刀”。他年轻的时候好手艺,街坊四邻都愿意找他磨刀,他磨得快,刀也快。从早上直干到晌午,肚子饿了,就近挑一家饭馆子,磨菜刀抵饭钱。饭馆里刀具多,而赵二吃饭无非吃个面条、顺序、炒饭、馄饨、饺子什么的,值不了几个钱,磨刀抵饭钱,划算得很,饭店老板没有不答应的。一来二去地,把远近的饭馆子都摸熟了,店家吃饭的时候,有时也邀他上桌喝点小酒,品评几道拿手好菜。赵二一开嘴,可把人惊着了,一道菜才搛了两筷子,就把这菜酸甜苦辣咸吃透了,这油盐酱醋下了多少,是多了少了,多了一勺还是半勺,他拿得准准的。就拿烫干丝来说,这干丝烫了几遍,是硬了还是软了,这酱汤里头酱油、麻油、鸡精、白糖、料酒,哪样多了哪样少了,他都说得分毫不差,可把人厨子唬得不轻。可他吃起东西来又狼吞虎咽,好没吃相,吃得又急又多——急是因为馋,多是因为磨刀需要卖两把子力气,这又让人不免有几分瞧不起,心里不免嘀咕:“这莫不是馋虫饿鬼投胎?”赵二“馋舌”的名声这才传出来。
陈五的舌头则与赵二不同,他的“刁舌”是养出来的。陈五是官家子弟出身,行五,是家里的老幺,打小活在蜜罐罐里,衣食无忧,后来他下海经商,人生才兴了波澜,这商业场里尔虞我诈的,他个初生牛犊哪见过这般风浪,折过本、倒过闭,栽了不少跟头,人到中年才在服装、食品生意上做出了成绩,生意做得大了,在全国各处都有业务往来,外省也开了几家分公司。他没什么嗜好,只是爱吃,打小就吃得顶好,从商后趁着出差的便利,把全国上下的美食都尝了个遍,那些个山珍海味、各色小吃,但凡说得上名儿的他都吃过。当然,他最钟意的还是家乡的淮扬菜,扬州城内各大名楼名店他都是常客,哪儿的小吃最地道他也门清儿,他有钱不惜金、爱吃不惜时,又好交朋友,名厨、小贩都乐于与他打交道。如今经济转型,生意不如以往好做了;他年纪也大了,身体大不如前,也就退下来,把生意交给子女打理。当他有更多的闲暇混迹于扬州城内的茶社、饭馆的时候,他的人生再次焕发出光芒。他几十年养下来的刁舌,混出了名堂。他吃过的好东西多了,又地道,让他对食物极为苛刻,味道、食材、火候但凡有一点不对,他一尝便知,他还有句口头禅:“这东西哪入得了口啊?”但他对食物的挑剔绝不因为食物的低贱或不健康,路边摊、大排档他向来不忌的,他的挑剔从来只因不地道。陈五不仅会吃,而且会做,他与扬州城里许多名厨都是好朋友,耳濡目染这么多年,早也看会了,这可就让他的舌头更“刁”了,一道菜有什么不对的,他不仅能尝出来,还能立马说出是在哪个节骨眼上里出了岔子,是食材处理不当,是火候拿捏不好,又或是调味品有差池,他总能一针见血。这也让他跻身为扬州厨界的名饕。
赵二、陈五俩人一贫一富,一匠一商,按说八竿子打不着,却因为都是个爱吃的主儿,而常常受邀试菜,这一来二去地也就混熟了。两人也都是坦荡人儿,这富的不嫌贫,这贫的也不惮人说他攀富,又都有闲,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好朋友。他这两条名舌搭在一起,更是相辅相成,如鱼得水。赵二虽然吃味儿准,但面见过什么世大面,从没出过扬州城就不说了,这扬州城里的名吃名菜他一个贫穷人家也不是想吃就能吃的;而陈五虽然遍尝天下美食,能吃能做,但这舌头上的神通到底还差了点。他俩一拍即合,成了形影不离的老哥们。
这日,陈五和赵二又在游春茶社里消磨了一上午,一壶绿杨春直喝到午饭边儿,他俩又商量起吃食来。赵二不很饿,就想吃个干拌面加腰花汤把中饭打发了,陈五却没什么主意,从香菇油菜、大煮干丝、韭菜长鱼丝、蟹粉狮子头一路念叨过来,没个想吃的,忽然陈五一拍桌子,叹了口气,道:“唉,要是还有扬州炒饭就好喽。”赵二听了只有好苦的份:“失传了十年的东西,还想它干嘛,现在哪还有人会炒炒饭呐!”陈五道:“唉,想当年炒饭大赛那时候,咱们这扬州炒饭多繁盛啊,三百多个炒饭师傅,个个能耐,一起来争这扬州炒饭国营饭店总厨位子。”赵二道:“哎哟,陈老弟,当年那炒饭大赛你也在呢?嗬,那多壮观呀!炒饭师傅在东关古渡边上一字儿排开,上百口锅灶炒了个热火朝天,光那油烟就能把人眼镜给糊住了,水边苍蝇蚊子多,可都给熏死了大半。据说这一天的用量,大米就费了近两百斤,海参、虾仁、火腿这些个好料都费了几十斤,嗬,可真是不惜本嘞。”
(如今的东关古渡)
“您二位知道当年的炒饭大赛?”却是邻座一位茶客问道。他们这一聊,把邻座给惊动了。
二人打量了一下来人,那人是个四十来岁的精壮汉子,倒不是茶社里相熟的常客,此时正两眼放光地望过来。赵二先接了腔:“那可不,那是80年的事了吧,那年老头我才十六七岁,瘦得跟个猴儿似的,倒便利了我。那人多多呀,亏得我精瘦,左钻右钻倒钻到了最里头,离那炒饭锅也就两米远,油烟一直熏到我脸上来,我旁边有个小四眼,眼镜都给熏糊掉了。”
“那真是太好了,麻烦您二位给我细讲细讲。我呀,是淮安人,也是个好吃的主,可真爱听这些个传奇故事!当年那炒饭大赛的事,我也有所耳闻,但细节却全不知道。还有您两位刚才说扬州炒饭失传了,可这大街小巷里不都还卖着扬州炒饭吗?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人激动说道,又带出来个疑问。
“嗐,那些个炒饭哪入得了口啊?”陈五说道,“可这说起前因后果来,可就长喽!这三十年前,扬州城出了个谢师傅,真是个妙人,年纪轻轻的就练就一身好本领,厨艺精湛、胆子还大,是咱淮扬菜的名厨,把许多淮扬名菜的菜谱都改了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而他最拿手的就是扬州炒饭,是行内公认的第一的,人人都说他的谢氏炒饭才配叫‘扬州炒饭’,是炒饭界的龙头、标杆。现在扬州的炒饭行当是不行了,群龙无首,没个拿得出手的人物。外地人问起哪家店的扬州炒饭最地道,咱都说是自个儿家的家常炒饭最好,全不把扬州厨界放在眼里。当年可不这样,有人问起最好的炒饭,可都说是这谢氏炒饭首屈一指,呱呱叫!”
“那炒饭大赛呀,就是谢师傅扬名立万的时候,那时候谢师傅还是个无名小卒,就是靠着在炒饭大赛上拔了头筹,才在厨界有了地位。这炒饭大赛呀,也不是无缘无故办起来的,是因为那个国营饭店老总厨去世了,位子空出来了,传人又没个准,这才在扬州城里大搞比赛,是为选继任人办的。”赵二接着说道。
“嗐,这传人有个准就能传呀,咱早就不是过去那封建了。哪能总由着他老子传儿子、师父传徒弟,国营饭店的总厨又不是他家的私厨。”陈五道。
“这说得也是。”赵二道,“不过也亏得如此,才有这炒饭大赛,嗬,真是了不得,扬州城多少年也遇不着这么大一场盛事。大半个扬州城的人都来看了,可真说得上是人山人海了。从早上直比到傍晚,比了不下六七场,一场指定一样炒饭,海参炒饭、虾仁炒饭、火腿炒饭、金裹银……三百个人一刷,剩一百,一百进三十,三十进十,最后比得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谢师傅,另一个好像是高邮还是宝应来的师傅,咱们不以成败论英雄,最后当然是谢师傅胜了。但我看那宝应师傅还有点子鬼六三枪,也是有本事的,好像年纪比谢师傅还要轻,可惜了啦,他的对手是谢师傅,最后惜败,也就离开扬州,不晓得走哪里去了。”
“这人我也记得,脸上有个大黑痣,怪吓人的,可有本事,差点就赢了。听说他原本在外地谋事的,特地赶回来参加比赛,匆匆忙忙没有准备周全。谢师傅同我是老相识了,他也说自己是险胜,就胜在以逸待劳。可以说比赛相当激烈呀,可惜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就是去看热闹,还不大看得懂里面的门道。”陈五也说道,“那个时候的扬州炒饭算是鼎盛时代,尤其是谢师傅当上国营饭店总厨之后,带出了扬州炒饭的辉煌,现在大江南北都知道扬州炒饭的名头,就是那个时候把名头给彻底传出去了。”
“既然这样,那您二位怎么说扬州炒饭失传了呢?”那汉子疑惑道。
“嗐,跟前任老总厨一样,没有传人。他这一死呀,娄子捅得比先前还大,他不仅没传人,还把谢氏炒饭的秘诀带进棺材里去了,没了这,炒饭就只得其形、不得其神,这一下把扬州炒饭的招牌都死没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呀,这可苦了我们这些老饕了,吃了几十年的炒饭,说没就没了,吃惯了谢师傅的炒饭,别家的炒饭谁还吃得下呀?”陈五说得直拍大腿。
“如今这餐饮业多兴旺啊,日进斗金的,哪家大厨不都是收几十个徒弟,咱扬州厨界咋还断层这么严重哩?”那汉子更是困惑了。
“这谁知道呢,谢师傅也不是没收徒弟,可谁都没有得他的真传,这老头轴得很,谁劝也不听,就是不肯传,说要把秘诀带进棺材里去。他亲儿子要学,他都不肯,硬把儿子逼到外地打工去了,我看他是老得糊恰恰了。”陈五道。
“说起来,他那道最出名的极品炒饭的滋味,我可现在都还记得。那饭用个顶好的瓷盘子端上来,颜色金灿灿,冒着白热气,上头零零星星见着五颜六色,青豆、火腿、虾仁、胡萝卜、小葱、冬菇、鸡丁、海参,摆盘摆成只金凤凰,还真挺漂亮。舀一调羹到到嘴里,那真是,感觉嘴里开了鲜味铺了,嗐,世上也没这号铺子,反正就是感觉那鱼、肉、虾、蟹、海带、豆豉、菌菇、蛤蜊全都聚到嘴里来了,能跟鲜字扯上关系的吃食好像都在嘴里炸了锅。”
“照你这么说,倒像味精放多了。”陈五打趣道。
“这哪能一样啊,味儿我可吃得多了。味精这玩意儿是从甘蔗、木薯、玉米里头提取的,鲜得单调,没啥变化。可极品炒饭的鲜味不一般,每样食材好像都有秘方处理过,每嚼着一样,就在嘴里头炸开一种味道。米粒的口感也刚刚好,吃着挺糯却又还挺有嚼头,一股椰子和玉米的香气直沁到米粒芯里边。”赵二一边说着,一边咂着舌头,口中啧啧有声。
那精壮汉子听得傻了眼,呆呆地看着赵二,正不知他是在讲奇幻故事还是在背书。陈五连忙解释,“老赵他这人味觉好,一般人吃不出这么细的味儿,你别听他的。”说着又向赵二道:“老赵,你吃的鲜味儿不是别的,正是谢老头的秘诀之一,我知道个大概,他用上等的羊肉、鲥鱼、刀鱼、虾蟹、新笋再佐以庆元的香菇、荣成的海带、霞浦的紫菜、永川的豆豉、阳江的蚝油和他秘制的酱油熬成了鲜汁,炒饭时只消倒一丁点下去,那炒出来的饭就能让人满嘴生鲜。可惜我不知道料的比例,也不知道他各色食材如何料理的,不然我也做些鲜汁来尝尝。”
那汉子听了早已心惊,道:“只是个酱汁已经这样繁复?您老不会言过其实了吧?”
陈五道:“就怕你不信,谢老头最好鼓捣这些,他的食材最是麻烦,他最得意的菜式里,几乎没几样原味的菜,都得特地弄出些奇味、怪味来,就算要用原味,他也会想些法子提味。川菜里的鱼香肉丝你知道吧,本是猪肉却偏要调出鱼味儿来,谢老头的菜多是如此,本是豆子却偏要做出肉味来,本是茄子却偏要调出鸡肉味来。《红楼梦》里头有道菜叫茄鲞,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那字儿比较生僻,读就读作日想夜想的“想”,本来是曹雪芹胡诌的一道菜,把不同时令的菜同时拿了来配这茄子,再用鸡油、鸡汤怎么来调。嘿,现在不是有大棚蔬菜了嘛,把这时令问题解决了,谢老头日想夜想,试了百多次,把曹雪芹原来的菜谱都改了,还真做出来了这东西。他请我吃过一会儿,哎哟,真是佛祖爷爷,那味儿真怪妙的,吃了一次就再也忘不下,搞得我也日想夜想,现在说起来也直流口水。真起了个好名儿,叫个茄鲞!”
《红楼梦》里的“茄鲞”
.....贾母笑道:"你把茄鲞(读音:xiǎng)搛些喂他。"凤姐儿听说,依言搛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刘姥姥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 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刘姥姥诧异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凤姐儿果又搛了些放入口内。刘姥姥细嚼了半日,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象是茄子。 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签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子一拌就是。"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
“就是,你可别不信,谢师傅的菜真是下了大工夫的,你知道他那一碟子炒饭卖个什么价吗?一百二哪!炒饭哪!还是十年前的价!要不怎么说寻常人家吃不起呢,像老陈这样的大老板才能常吃,像我一穷二白的,这么些年统共也就吃过两回,一回是年轻时结婚,再一回就是四十岁过生日,等我五十岁过寿时,炒饭早失传了,再想吃也吃不着了。”赵二道。
汉子咋舌不已,却冷不丁叹了口气,道:“唉,要是谢师傅还在就好了,被您二位这么一说,我的馋虫也给勾出来了。”
“嗐,别说是你,我们都有十来年没吃过了。”赵二道,“谢师傅已经过身可怎么也指望不上了,我这些年呀,就心心念念地盼着当年谢师傅的手下败将——那个宝应师傅能回咱扬州来,我记得他可比谢师傅年轻好几岁,没准如今还硬棒,厨艺还没落下。”
“对对对,那个大黑痣,”陈五说着往右颊上一点,“他有标记,倒也好认,只是人海茫茫,上哪儿找去,又不见得他还上扬州来。”
那汉子却是一愣,眼睛直盯着陈五右颊上置点过的地方,笑道:“天底下真有这么巧的事儿!我上个月出差到泰州,还真在一家饭馆子里见过一个有大黑痣的老头!不过,那老头好像不是厨子,只是在店里闲坐。他家的炒饭我吃了,还算可口,但可不像您二位刚才说谢师傅那样玄乎。”
“不是厨子你说他干嘛,八成是个……”赵二嘀咕道
“那老头的黑痣是长在什么地方?”陈五倒来了兴致。
看陈五真当了回事,那汉子倒有些心虚,道:“只记得是右边脸上,具体什么位置,真不记得,当时以为是个大苍蝇才多盯了两眼,发现是个大痣也就没好意思再看。老头的样貌我倒还有点印象,是个塌鼻子、小眼睛,年纪看起来挺老,得有六十大几了。”
陈五、赵二一时都有些踌躇,拿不太准。三十年前见过的人,能记得有个大痣就不错了,谁记得清样貌,何况三十年过去了,人变鬼、鬼变人,谁知道如今变成什么样。
陈五不自觉地站起来,背着手四下踱步,忽然两手一拍,道:“不行,我必须得看看去。你给我说说那饭店的位置,我这会儿就开车过去。”
“还当真呀,我看也就凑巧也是个大黑痣罢了。你还是省了这趟工夫吧,何苦白跑这一遭呢,汽油钱都得费不少。”赵二道。
“你还不知道我呀,不弄清楚这事,我能吃得下饭?正好利用吃饭这点工夫跑一趟泰州,也不远。”陈五道。
“我跟着同去吧,我也正想再一探究竟呢。那饭店就开在塘湾镇上,到了地方我来指路。”那汉子也附和道。
“哎唷,你俩都去,那把我也捎上吧,可我现在饿得慌,要不咱吃了再走吧。”赵二道。
陈五低头看了看表,道:“现在还不到十二点,咱到了地方再吃,也不过两点,饿不着你肚子里的馋虫。”说罢揪起赵二就出了店门。
陈五的小汽车就停在不远处,是辆奔驰,那汉子才知这老陈是真有几分阔绰。
路程倒真是不远,不过两个小时,便到了镇上。一路上三人有说有笑地胡侃瞎聊,倒添了些了解。那汉子姓黄,叫黄广发,是个小个体户,卖毛绒玩具的,陈赵二人都笑他五大三粗个汉子,倒捯饬这些个玩意儿,黄广发却只憨笑,说是为混口饭吃。黄广发在他们当地也算是个老饕了,只不过跟陈赵两人一比,既差着辈分,更差着功力。这次到扬州是去五亭龙进货来了,上午刚把事情谈成,只不过寻个地方喝口茶,就逛到了游春茶社,却听见邻座在聊炒饭大赛,一下子把他勾住了,这才有了现在这事儿。
黄广发有些不大认得路,东指西指地引着车儿在镇上瞎转悠。车子越走越离开热闹处,直走到田间村舍边来,忽见前边僻静处依山傍水,杨柳青青,竟有家独户的酒楼,远看着有些老旧,却也透着些古味,别具特色,门前挂一面大酒旗,被风吹得皱来皱去,依稀可辨旗上四个大字——扬州炒饭。黄广发眼睛一亮,“对了,就是那儿,门口挂着酒旗的那家。”
陈五驾着车急忙驶过去。到了店前,三人下得车来,却是一愣。原来,店门口竟挂了丧。
(未完待续)
我当然会一直笔耕不辍。
并不管是否有人看这些文字。
我自知它的价值。
(关注公众号——蝉蜕文创室)